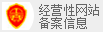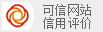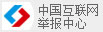在旧时,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好贵古贱今。凡今人作了什么好事,这些人总觉得无论这事如何好,或作得如何好,但比之古人,总要差一点,古人所作的事,一定更好,或作得更好。如果今人作了什么坏事,这些人便借题发挥,用“世风不古,人心日下”等滥套,将今人骂得“狗血淋头”。
在旧时,除了些庙堂颂圣的作品外,在私家著作里,很少看见称赞他自己时代的文章。王充《论衡•齐世》篇说:“古有无义之人,今有建节之士,善恶杂厕,何世无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辩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近有奇而辩不称,今有异而笔不记。”王充看出了大部分人的错误,所以他在他自己的书里有《宣汉》篇。在这篇里,王充指出,汉朝的文治武功,都超越前古。王充感觉到他自己的时代的伟大。这在旧时是很少见的。
在旧时,大部分人所以都贵古贱今者,其原因有两点可说。就第一点说,大部分人本来都是“贵所闻而贱所见”。“今”是一个人之“所见世”,“古”是一个人之“所闻世”,或“所传闻世”。大部分人本来都是“贵所闻而贱所见”,所以他们亦是贵古而贱今。《抱朴子》说:“俗世多云: 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之患矣。”正是说此。
就第二点说,中国旧时社会,是农业的社会,在农业的社会里,人所注意的事情,如四时之变化,五谷之种植收获等,大部分都是循环的。对于循环的事情,人靠经验即可以知之、治之。农业社会的人,特别“尊高年”。高年是有经验的人。青年人有什么不了解或不能应付的事,即请教于高年。高年,凭他的经验,可以教训青年,而这些教训,大致都是不错的,因为在农业社会里,新来的事与过去的事,大致都是一类的。在这种情形下,人对于“古”即不知不觉地起了一种尊敬之心。
但在工业社会的人,新的事情,时常发生。而其新又不只是个体上的新,而是种类上的新。我们常听见有些高年人说:“这种事我没有经过。”这一类的话,在农业社会里,是很有意义的,但在工业社会里,则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因为在工业社会里,人所没经过而新有的事,是太多了。对于人所没有经过的事,旧经验的教训即不可用,至少是不一定可用。所以在工业社会里高年不是一个傲人的性质,而青年反是一个傲人的性质了。青年所以成为一个傲人的性质者,因青年对于种类上的新的事物,可以学习,而高年则不能学习也。在农业社会里,人所以尊高年,一半是由于道德的理由,一半是由于实用的理由。在工业社会里,如果人亦尊高年,其所以尊高年完全是由于道德的理由。
近数十年来,中国自农业社会,渐变为工业社会,所以贵古贱今的人,在现在是很少的了。但有一部分人另外又犯一种毛病,即贵远贱近。凡中国人做了什么好事,这些人总觉得,无论这事如何好,或做得如何好,但比之外国人,总要差一点。他们总想着,外国人所做的事,一定更好,或一定做得更好。如中国人做了什么坏事,这些人一定要借题发挥,用“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等滥套,把中国人骂得“狗血淋头”。
现在所以有这一部分人,贵远贱近者,其原因亦有两点可说。就第一点说,近是人之所见,远是人之所闻或所传闻。人既易于“贵所闻而贱所见”,所以也易于贵远贱近。
就第二点说,中国现在一部分人还有殖民地人的心理。中国人有这种心理,以在清末民初时候为最甚。相传有人以为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这与上《抱朴子》所说,可谓“异曲同工”。实际上或不必真有人如此以为,但有此传说,也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实。此事实使我们知道,当时有许多人盲目地崇拜西洋人。这种殖民地人的心理,在中国到现在还有残余。此即是说,到现在还有一部分中国人多少有殖民地人的心理。贵远贱近,虽亦是人之常情,但他们又并不是仅只贵远贱近,他们对于阿比西尼亚的英勇,总觉得“不过如此”,而对于捷克的怯懦,总觉得“没有什么”。在这些方面看,这一部分人的贵远贱近,是由于他们的心理,是殖民地人的心理。
就人之常情说,人贵所闻而贱所见。这并不是人的弱点,而正是人的优点。“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其一即是人有理想。我们可以说,人是有理想的动物。就客观方面说,理想是事物的完全的典型。就主观方面说,理想是人对于事物的完全的典型的知识。人有理想,而其所见的事物,都不尽合于他的理想。社会上或历史上的事,都是人做的。人都是人,不是神。此即是说,没有人是绝对完全的,没有人是完全合乎人的定义的。
在实际的世界中,无论什么事物,都必多少合乎它的定义,但亦没有一个事物,能完全合乎它的定义。人既是实际的事物,他总有缺点,他所作的事亦总有缺点。在时间上或空间上离我们远的人,亦有他们的缺点,他们所作的事亦有缺点。不过这些缺点,异时异地的人,因为距离远的缘故,不容易看见,因为距离远的缘故,人看异时异地的人或事,都只看见其大体轮廓,其详细则看不清楚。如其大体轮廓无大缺点,人即以为其是完全的。人对于其同时同地的人或事,则是深知其详。因深知其详的缘故,不但看不见其大体轮廓的无大缺点,如果其大体轮廓是无大缺点,而且简直看不见什么是其大体轮廓,如所谓见树不见林者。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看其同时同地的事,自然只见其是不完全的了。
我们论历史上或社会上的事,必须先就其大体轮廓看。看见了它的大体轮廓,然后可以看见它的主要趋势,及它的趋势所向的目的。用我们以上所用的名词说,我们看见了它的大体轮廓,我们才可以于它的许多“情”中,看出它的“性”。
◎本文摘自冯友兰《新事论》,转载请注明。
来源:大道知行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3289 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3289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