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手机继续浏览本文,也可以分享给你的联系人。

在手机继续浏览本文,也可以分享给你的联系人。
在这个物质前所未有丰富的时代,“买买买”早已不只是为了生存,而是关乎一个人的兴趣、品味,乃至于人生观。当“一切坚固都烟消云散”,许多人是从“玩物”中找到了满足感和自我价值,于是,“玩物丧志”的古训似乎到了该重新审视的时候。
有人为这个物质时代下了一个美好的注脚——玩物立志。文章大意是说,物质时代前所未有的“丰盛”,带来了消费升级和消费民主,而玩物立志就是这个时代的生活趋势,它既是摆脱“物质奴役”的生活哲学,又能帮助人们脱离蝇营狗苟的日常生活,活出此岸的“诗和远方”。
听起来,诗和远方,乐趣和志向,真是唾手可得的事情。而且获取方法酷炫无比——只要你会买会玩。
是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点点小欲望的满足,一点点小确幸就已经让人欣喜不已。但生活就是生活,非要将物欲扯上立志,顿时落于下成。物欲时代刚刚杀到,不应预支后物欲的超脱逻辑来应对当下的困境。它为时尚早,因而并无实效。
撰文 | 冯柒
用励志的名目,耍消费主义的流氓
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是前所未有的物质丰盛,中国的现状符合让·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的基本判断。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随着消费的不断升级,我们确实享受到了消费社会经济民主化带来的平等和愉悦。

《消费社会》
作者:[法] 让·波德里亚
译者:刘成富、全志钢
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5月
然而,物质生活丰富之后的消极面是消费让人沉溺,物欲的暴涨直接导致血槽被掏空和幸福感被消解。热文作者并未否认这一点,让人无法理解的是,面对消费社会带来的物欲增长,竟然祭出一招“玩物立志”,并且将之当作唯一的拯救手段。
我们已经来到后物欲时代了吗?讲真,以当下的消费面貌,真的无法昧着眼睛说瞎话。炫耀性消费要走到尽头还为时尚早,“人类将在游戏中解决消费主义的弊端,过上诗意的生活”,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消费主义的蛊惑,消解钱包干瘪的负重感。
目下的各式消费生活报告所呈现出来的消费细分和消费升级、兴趣消费和休闲消费的增长,并不足以作为“后物欲时代”的证据,顶多只能彰显一种“消费的时髦”。它反而十分贴切地印证了瓦尔特·本雅明在谈及世界博览会时的论断:“他们创造了一种使商品的使用价值退居后台这样一种局面。他们打开一个幽幻的世界,人们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精神解脱。”

电影《春娇救志明》中,张志明花9万5买回达利的“手指公”摆设。
波德里亚讨论“消费的神奇地位”时明确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消费的益处并不是作为工作或生产过程的结合来体验的,而是作为奇迹。意思就是,消费社会所信仰的幸福,只是幸福标志的积累。他甚至直接戳破电视的“造神”假象,并且称之为“骗取”。
“玩物立志”是另一个升级的幻想。我们肯定“玩物”能够使人从苟且的日常中解脱,但之后一定是通往“诗和远方”吗?
当消费升级仍然停留在“附加性消费”的范畴里,“玩物立志”也只能是本雅明所说的“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涂脂抹粉”而已。

《巴黎,19世纪的首都》
作者:[德] 瓦尔特·本雅明
译者:刘北成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3年3月
玩物就是玩物,为什么要立志?
消费主义的幻象只是表面的迷雾,“玩物立志”还隐含了内面的陷阱:成功学。
我们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渴望成功。这个时代充斥了各种急求上进的人,他们为各种模糊不清的价值标准拼命奋斗,而以成功学身份出现的各种培训班和提升课程也在努力地推销它们的理论体系。
现在的人所接受的成功观越来越狭窄。我们尽可能多地使用靠近成功的正面词汇,比如开发潜能、拓展人脉、修心、沟通、营销、细节、感恩、提升、励志等等。从广告到朋友圈都充斥着正能量的语言,足以造成一种全民大步往前迈向成功的错觉。
与此同时,成功观的辐射面则越来越宽泛。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成功、我们要什么成功、可不可以不成功,只能尽可能多地将“成功”的边界无限延伸,其中便包括“玩”——玩也能玩出成功来,“玩”就这样具备了合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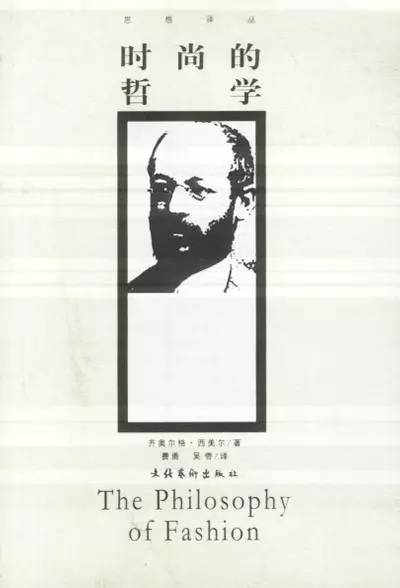
《时尚的哲学》
作者: [德] 齐奥尔格·西美尔
译者: 费勇
版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年9月
有人将“玩”分作广义和狭义,狭义的玩固然是把戏,广义的玩则是生活情趣和艺术,它能培养情趣、对抗时光、生成乐趣,甚至立下志向。这种将“玩”的外延也无限扩展的做法,恰好与“成功”无限延伸的边界重叠,重叠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玩物立志”。这么听起来,玩不但有合理性,而且还有必要性——毕竟,玩物也是一种志向啊!
这种论述技巧有毒。在消费逻辑上,人们可以通过玩物追求当下的幸福和永恒的快乐,但是不能推导出“立志”的必然结果,更不应以“立志”为目的来要求“玩物”。
当成功变成“玩物”的蛊惑和胁迫,“玩”的乐趣就被彻底瓦解了。打个比方,玩绘画、玩摄影、玩电脑、玩音乐、玩书法、玩花艺……如果一个孩子能够沉迷于“玩”,玩出名堂不是问题;若以“立志”为名,以培养情趣和志向为目的要求孩子玩以上的任何玩意儿,对于孩子而言,这都不叫“玩”,而是一门通向“成功之路”必须的功课。

“玩音乐”往往被和培养特长和志向绑为一体。
恰恰是“丧志”,让“玩物”有了意义
只有辨认出“消费主义”和“成功学”的双重陷阱,才能好好谈“玩物”。
“玩物”可能成为“诗和远方”的开始,但它有一个必要前提:必须脱离物欲性的诱惑和匮乏感的焦虑,同时摆脱“立志”的桎梏。
当你还在为群体性的购物狂欢而欣喜的时候,玩物带来的“诗和远方”只是一种幸福的幻觉。而你,“有欲望而备受经济压抑、购物而滋生幸福迷狂”,充其量只是文化学者周志强所说的“新穷人”,即“在生机勃勃而不断上涨的消费商品中变成了穷人的那一类人”。
而社会学家郑也夫所说的“后物欲时代”,尚未来临。他认为人类能在游戏中解决消费主义的弊端,但这种“游戏”必定不是来自于对新事物的歌颂。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作者: 郑也夫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
在消费社会里,对物的好奇心带有激情的表象,但是波德里亚认为,它的本质是一种“介于冷漠和迷恋之间的东西”,而且“与激情相对立”,他称之为“游戏式好奇心”。
如果人与物的关系本身还是着迷和操纵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和爱好者与艺术作品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尽管这种游戏式的活动具有激情的表象,但消费是组合式投入,并且排斥激情。
“玩物”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哲学,是轻与重的结合。
重,是对人生有十足的热情和投入。这种着迷跟操纵无关,纯然是热爱燃起的激情。好而不据,不为所囿。
轻,是把“玩”回归到“玩”本身。不附加任何的“志向”之重,与成功无关,甚至有点二。可是人生不二一点,也没什么好玩的。可以这么说,玩物的意义,是人生之轻的意义。
文物收藏家、鉴赏家王世襄是大玩家,书法家启功称之为“玩物立志”的典范。王世襄在2006年接受电视节目《可凡倾听》采访时说起,直言自己不敢当,“说实在的,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我全玩儿了,而玩儿是必定丧志,不可能励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