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手机继续浏览本文,也可以分享给你的联系人。

在手机继续浏览本文,也可以分享给你的联系人。
台湾电影的艺术成就被公认斐然。詹宏志监制了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吴念真的《多桑》等多部经典名片,李安的第一部电影和他也大有关系。与此同时,他还是侯孝贤和杨德昌的背后金主。梁文道甚至说:“没有詹宏志,能有今天的台湾?”在与我们特约记者的访谈中,詹宏志将新电影运动的许多细节娓娓道来,让我们看到这背后的力量到底在哪里。
携新书《旅行与读书》,台湾著名文化人詹宏志去年年底来到北京,在北大与梁文道对谈。
詹宏志被梁文道称为“绝代才子”,早期在滚石唱片担任企划,策划了台湾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场演唱会,让罗大佑的摇滚乐冲击了整个台湾音乐,亦成为罗大佑的挚友。然而他更重要的影响力在于电影界。
上世纪70年代,他就是台湾新电影的重要舆论推手,起草了举世瞩目的“台湾新电影宣言”,并且监制了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吴念真的《多桑》等多部经典名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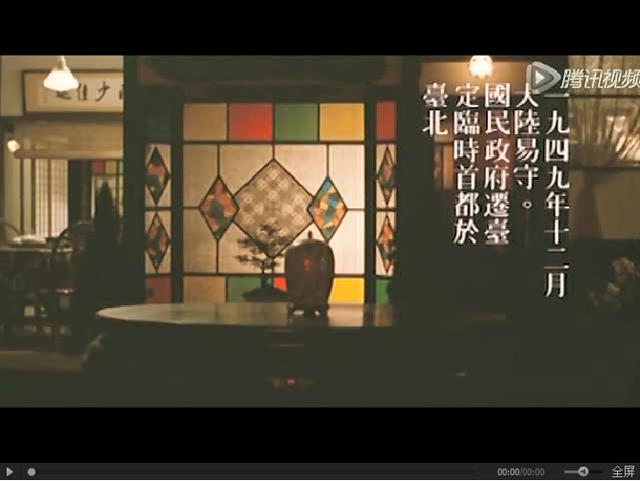
《悲情城市》
他是侯孝贤和杨德昌的背后金主,侯孝贤的《冬冬的假期》上映时票房惨淡,连带把他个人的财务也拖垮了,朱天文说:“我们要不要去找一下詹宏志,看看他怎么说?”詹宏志成了侯孝贤的救命稻草,和梁朝伟的经纪人谈他的档期,细到什么程度?连一天要洗几件衣服合同上都写清楚。因为有了詹宏志,侯孝贤得以腾出手来潜心于电影制作,并在国际影坛大放异彩,可以说没有詹宏志这位监制,是绝不可能的。
而梁文道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没有詹宏志,能有今天的台湾?”

《悲情城市》(1989)剧照
台湾新电影运动:从观众变成参与者
河西:1982年的《光阴的故事》被认为是台湾新浪潮电影革命性的第一枪,当时你在美国不在台湾?
詹宏志:我是1983年回到台湾来的,没有赶上。后来新电影运动的核心人物小野和吴念真两个人说你来电影公司的试片间,我们把这一年里面的要紧的电影全部放给你看。我去了,看了当时的《光阴的故事》、《小毕的故事》和《在那河畔青草青》。
河西:后两部是侯孝贤早期的作品,当时看到它们的时候什么感受?
詹宏志:当时侯孝贤和陈坤厚两个人合作的那一系列作品,我看得很震撼也很兴奋,我觉得到这一刻为止,我还是一名观众,因为在媒体工作的时候,在1981年前,我曾经是台湾介绍香港新浪潮最积极的媒体人。所以电影圈里的朋友知道有我这个人,那是因为我是一个媒体人,并不是因为我参与电影制作。
可 是1983年我回来之后没多久,台湾就碰到了新电影运动里的一个关键性事件,即所谓的“削苹果事件”。这个事件是这样的,1983年底有一部重要的新电影 作品《儿子的大玩偶》,这是一个三段式的电影,全部由黄春明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第一段就是“儿子的大玩偶”,侯孝贤拍的,第二段由曾壮祥导演,第三段则 是万仁拍的“苹果的滋味”。

《儿子的大玩偶》剧照
这个片子的出品方是台湾的中影股份有限公司,中影是个“党营事业”嘛,这个片子拍完之后,国民党的文工会主委要审查,他一看就非常生气,觉得这部片子完全是在揭露台湾丑陋的一面。我们现在看70年代台湾电影,琼瑶片,都比较虚幻、唯美,那是当时台湾电影的主流。
可是台湾新电影不同,他们是有写实的企图的,一个社会如果不让人批评,写实就变成控诉。有时候你一写实到某些比较尖锐的社会真相,那看起来像是对政治的批判。所以当时这部电影出来之后,国民党内部就有意见,觉得它有问题不能公映。
电影公司里的朋友把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新闻业了,可是我在新闻业的影响力还在,当时《中国时报》负责研究版的主编就是我原来工作的搭档,我就找他商量说,这个事我们能做什么?最后我们俩连夜写了一整版的文章,声援台湾新电影,希望这个电影不要胎死腹中。
这篇文章刊登出来之后,第二天变成了大事件。国民党觉得影响不好,就妥协了,让电影公映,可是我的朋友受到上方的压力只好辞职,媒体就不让干了。但我们写这篇文章之前完全明白这样做的后果,他发好稿之后,辞职信都写好了,就放在抽屉里面,随时有人找他,他就把它拿出来。这是当时的事件前后,自那之后,我就从一个观众变成一个参与者。
河西:1986年的11月6日,杨德昌40岁生日,在杨德昌家里的party上起草了《台湾新电影宣言》,可以说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你起草的,怎么会起草这份宣言的?
詹宏志:杨德昌生日那天实际上我不在,因为正好我父亲病危了,在台湾中部城市的一个加护病房里面,我只能在病床旁边陪护我的父亲。
台湾那一批电影工作者对当时保守的社会氛围不满,像杨德昌、侯孝贤当时都没有电影可拍,他们很愤懑,希望通过宣言的方式来表达意见,但是当天在杨德昌的生日宴上并没有形成文字,只是达成了共识。然后他们派人来找我,他在我家门口等我,等了整整一个晚上,因为我第二天才回台北,回来之后我正好在门口遇见他。他跟我说:他们想要一个宣言,你可以帮我们拟一个稿子吗?
我当时也没有就答应,他前脚刚走,我父亲那边电话又来了,我父亲的病情恶化了,我得知父亲昏迷的消息,急急忙忙赶去医院。在病床边陪伴我老父亲的时候,我无事可做,忽然想起朋友的嘱托,所以我就拿起笔来把宣言写了,然后由侯孝贤、朱天文、朱天心等人签字,签字的一共有40多个人。
河西:这份宣言对台湾新电影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刺激。
詹宏志:恰恰相反。电影宣言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不满意。每一个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觉得这个宣言重了,有的人却嫌这个宣言太温和,太软弱了,这样子哪像革命嘛。有的人心里害怕,说我在上面签了字,我以后还有工作吗?有担忧。所以宣言不写还好,写完之后大家之间的真正的差异就明朗起来。原来新电影运动初期,大 家相互帮助,从此之后就各奔东西了,四分五裂是从这里开始的。
所以杨德昌就说这其实是结束的开始(Beginning of the end),那个美好的运动气氛是瓦解了。

《光阴的故事》剧照
监制《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从万分沮丧到热泪盈眶
河西:怎么担任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监制的?
詹宏志:有一次,杨德昌对我说,他想要拍朱天文的小说《带我去吧,月光》,我说好啊,找到中影谈,带回1400多万台币。一开机,我才发现,杨德昌要拍的,已经不是 《带我去吧,月光》,而是后来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也就罢了,片子没拍完,钱先花完,不够,怎么办,请我帮忙。我实际上做的这个监制,就是筹钱的活。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我问他:“还需多少钱?”他说:“210万,有了,一定拍完。”我说:“好”。与中影谈判。中影觉得,大导演拍片,预算不够也是常有的事,再支210万台币给我们。结果,没拍完,钱又花光,我问杨德昌:“你再仔细算一算,全部拍完,一共需要多少钱?”
他仔细算过,告诉我:“需要1000万。”
1000万,可是个大数目,我硬着头皮再找到中影,中影这回意识到了风险,一口回绝:“不行!”
我感到万分沮丧,又如坐针毡。怎么办?讨不到钱,片子完不成,前面的所有投资都要打水漂,自己这个中间人可得担责任。真是快绝望了,幸好,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家日本公司居然给我说动,我不仅把投资所需的资金填补上,还赚了。
当影片终于完成上映之后,我看完电影热泪盈眶:“真的,看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之后,我觉得一切的辛苦、担忧都是值得的,这真是一部伟大的电影。《牯岭 街少年杀人事件》表面上是60年代台北少男少女的爱情故事,背后则是整个时代、整个种族之间的冲突,本省和外省之间各式各样的冲突。他有一个那么大企图在。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剧照
河西:台湾新电影都是文艺片,有些还比较晦涩缓慢,它们有亏钱?
詹宏志:我参与的一部都没有亏,全部都赚钱,有的打平了。收益最大的是《悲情城市》,因为《悲情城市》得了威尼斯影展的金狮奖,它是台湾第一部得这样的大奖,所以效益最大,《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得到柏林影展的评审奖,对市场的作用不大。
只有《悲情城市》效益非常非常大。它开启了电影投资回报新的计算方法,新的投资跟新的回收的方法。这种工作方式形成之后,一直到今天为止,侯孝贤也没有任何拍片的资金的问题,这个资金都是国际上来的,多种资金合起来,每一部戏都能打平,都是因为这种模式。
帮助李安拍第一部电影
河西:好像李安和你也有关系?
詹宏志:李安比较晚,他已经不能算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参与者了。不过他拍电影和我也有点关系,我在纽约时就认识他,他所有的戏都是在纽约拍的,只是我把他的剧本带到台湾来,得了奖,然后中影愿意投拍他的戏,就是他的第一部电影《推手》。

《推手》剧照
中影给他的预算很少,所以他有点不清楚这点钱够不够,拍不拍得成。他来问我,我跟他说,我一个人对电影的事了解得没那么多,我给你办个party,到我家里吃饭,我邀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他们都来,他们每个人有不同的经验,你让他们给你出出主意。
我说虽然新电影大家已经有一点分崩离析了,不过我还是唯一能把大家找在一起的人。所以大家那天也都来了,每个人就给了意见,有这个意见、那个意见,最后侯孝贤跟李安说,你不管是哪种预算都得拍,因为这是你的第一部电影,我们所有人都这样过来的。
所以这句话给了李安很大的鼓励,李安第二天就打了电话给我说,他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了。然后他就带着当时的预算47万美金回美国,找了他在纽约伊利诺伊大学的 学长James Schamus。他这个学长刚刚开了一个制作公司,也没拍过戏,两个人一商量,把所有的钱都花在电影上,大家都不拿钱。
我们和中影谈了一个事后分成的计划,以后再拿钱,因为这个片子花的钱是太少,所以这个片子光在美国大概就卖了1600万美金,而它是50万美金拍的电影。所以他就被美国选成“年度最佳独立制作”,因为太有效率了。
河西:有一种说法认为,因为台湾新电影太文艺化了,或者说太个性化了,导致了台湾电影市场的萎靡不振,你怎么看?
詹宏志:我觉得他们开始出现的时候死胡同早到了,台湾电影公司都是没了,基本上没了,那时候只有香港电影了,台湾根本没有戏在拍,还拍戏的只有这些人。我举个这样的例子,拍这个《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因为里面有帮派、有枪战,为了拍一个枪战戏,我得从香港租道具枪。
因 为台湾没有电影在拍了,所以所有的剧组,所需要的这些资源都没了,你要道具,你哪里找枪?根本就没有。就是有了枪也没用啊,开了枪要炸开来,你得要有爆破组,我们到哪里去找爆破组?台湾没有戏怎么会有爆破组,我去香港找爆破组,香港说没办法,当时《英雄本色》正红,一开几十部枪战戏没人有空。

《英雄本色》剧照
我找找找,最后找到菲律宾去,菲律宾有很好的、高水准的爆破组,哪儿来的?是当年大卫科波拉在菲律宾拍《现代启示录》,带了好莱坞人去,训练了一批当地的人。这戏拍走了,剧组还留在那儿,所以有这样的技术。戏拍完了,做后期制作,哪里做?杨德昌到欧洲去做,侯孝贤到日本去做。台湾哪有?
我说这个话批评他们公平吗,电影工业已经没有了,只有这样的艺术创作咬着牙还能干,其他哪有人能做这个事?没有人做这个事。台湾所有的电影资金全在香港,任何片商都是钱多的是,要是刘德华的片子,那我出八百万,我出一千万,你是王晶要开一部戏我出多少钱,徐克你要开一部戏我出多少钱。
台湾已经变成是香港制片的一个分摊者,本地没有供应。那这些片子还能维持这个格局,到今天台湾电影还有命脉可循,还可以出现魏德圣这一批人,魏德圣是杨德昌的副导,钮承泽是侯孝贤的演员。后来所有的导演,每一个追溯全是当年新电影的工作者,今天台湾电影才有恢复的可能。没有这个新电影把这一丝命脉给留住,那你根本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