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手机继续浏览本文,也可以分享给你的联系人。

在手机继续浏览本文,也可以分享给你的联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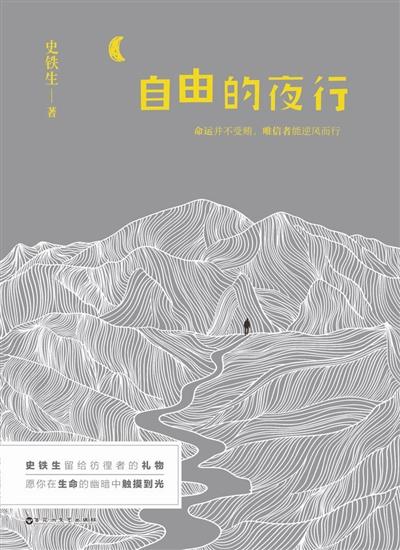
《自由的夜行》,史铁生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紫图图书, 2016.11
史铁生散文集《自由的夜行》近日面世,该书从史铁生浩瀚的文集中精选30篇散文,除却《秋天的怀念》、《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病隙碎笔》这样家喻户晓的经典文本,更包含《我二十一岁那年》、《复杂的必要》、《乐观的根据》等散见于全文集而尚未被大众熟知的精彩篇章。
在这本书里,史铁生不再只是那个在地坛深切怀念母亲的人,不再是那个背负着沉重的生命枷锁踽踽独行的行路人,他更是一个有着说走就走看天下的心的年轻人,一个碎碎念的影评人,一个教人如何对待爱情的老司机……在这里,史铁生更接近一个为了生活不断奋斗的朋友:纵使轮椅不能代替双腿,但仍然可以让生命飞翔;即使明天就要死去,也要把日子过成诗。
复杂的必要性
母亲去世十年后的那个清明节,我和父亲和妹妹去寻过她的坟。
母亲去得突然,且在中年。那时我坐在轮椅上正惶然不知要向哪儿去,妹妹还在读小学。父亲独自送母亲下了葬。巨大的灾难让我们在十年中都不敢提起她,甚至把墙上她的照片也收起来,总看着她和总让她看着我们,都受不了。才知道越大的悲痛越是无言:没有一句关于她的话是恰当的,没有一个关于她的字不是恐怖的。
十年过去,悲痛才似轻了些,我们同时说起了要去看看母亲的坟。三个人也便同时明白,十年里我们不提起她,但各自都在一天一天地想着她。
坟却没有了,或者从来就没有过。母亲辞世的那个年代,城市的普通百姓不可能有一座坟,只是火化了然后深葬,不留痕迹。父亲满山跑着找,终于找到了他当年牢记下的一个标志,说:离那标志向东三十步左右就是母亲的骨灰深埋的地方。但是向东不足二十步已见几间新房,房前堆了石料,是一家制作墓碑的小工厂了,几个工匠埋头叮当地雕凿着碑石。父亲憋红了脸,喘气声一下比一下粗重。妹妹推着我走近前去,把那儿看了很久。又是无言。离开时我对他们俩说:也好,只当那儿是母亲的纪念堂吧。
虽是这么说,心里却空落得以至于疼。
我当然反对大造阴宅。但是,简单到深埋且不留一丝痕迹,真也太残酷。一个你所深爱的人,一个饱经艰难的人,一个无比丰富的心魂……就这么轻易地删减为零了?这感觉让人沮丧至极,仿佛是说,生命的每一步原都是可以这样删除的。
纪念的习俗或方式可以多样,但总是要有。而且不能简单,务要复杂些才好。复杂不是繁冗和耗费,心魂所要的隆重,并非物质的铺张可以奏效。可以火葬,可以水葬,可以天葬,可以竖碑,也可为死者种一棵树,甚或只为他珍藏一片树叶或供奉一根枯草……任何方式都好,唯不可意味了简单。任何方式都表明了复杂的必要。因为,那是心魂对心魂的珍重所要求的仪式,心魂不能容忍对心魂的简化。
从而想到文学。文学,正是遵奉了这种复杂原则。理论要走向简单,文学却要去接近复杂。若要简单,任何人生都是可以删减到只剩下吃喝屙撒睡的,任何小说也都可以删减到只剩下几行梗概,任何历史都可以删减到只留几个符号式的伟人,任何壮举和怯逃都可以删减成一份光荣加一份耻辱……但是这不行,你不可能满足于像孩子那样只盼结局,你要看过程,从复杂的过程看生命艰巨的处境,以享隆重与壮美。其实人间的事,更多的都是可以删减但不容删减的。不信去想吧。比如足球,若单为决个胜负,原是可以一上来就踢点球的,满场奔跑倒为了什么呢?
太阳向上升起

史铁生(图源于网络)
当导演真是比当作家难。写作是个体经营,败了,顶多饿死一口儿。拍电影是集体项目,上千万的投资,数十人的生计,导演是集艺术与财政之责于一身。可艺术与财政从来就有冲突,前者强调个性,后者为求利润不得不迁就大众口味——这本身就像个悲剧:相互冲突的双方都值得同情。怕只怕一味求利,结果是火了一宗产业,灭了一门艺术。电影,尤其声色犬马、名利昭彰,不像写作,天生来的是一种寂寞勾当。然而大隐隐于市。在这汹涌的市场激流中,匹马单枪杀出个姜文来,直让人感叹造化不死。
姜文岂止是艺术家,更是位哲人。哲人,未必就要懂得多少哲学,或魔魔道道地只在逻辑中周旋。先哲有言:“哲学不意味着一套命题、一种教义、甚或一个体系,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为特殊的激情所激发的生活。”怎样的生活方式?善思考,或如柏拉图所说:爱智慧。怎样的激情呢?爱,或如艾略特所说:爱是一种折磨。折磨何来?不能容忍生活总就那么“白云千载空悠悠”,而要探问那云之空处的悬难。张越说:能据不同时期的作品,看出其心路历程的导演,在中国只有姜文一个。此即折磨的价值。
姜文的前两部作品,已见那折磨之于个例。这一回,折磨走向了形而上——《太阳照常升起》,实在是说:如《浮士德》般的生命困境,一向都在人间。
两个年轻女人,在一块指向“路尽头”的标牌前分手,一个去完婚,一个去为丈夫奔丧,一个以为从此幸福美满,一个不失浪漫地要孤守到白头。这应该是故事的开始,但姜文把它放在了影片的最后。而影片的开头,实际是故事的结尾:多年以后,以为幸福美满的一个,生活陷入了无聊与委琐;孤守白头的一位呢,竟至疯狂,后随一条满载“光荣历史的河流”不知去向。
如果1、2、3、4地平铺直叙,2007年只会像以往一样,在众多惨痛故事的旁边再添上一个。而现在,4、2、3、1,中国影坛随之有了一个真正的悲剧。
最后一幕,太阳照常升起,谁说那是光明的尾巴?那是故事的开始呀!这可不是简单的倒叙。结束,等于开始,那是说:生活,曾经是这样,将来未必就不是这样,“太阳底下本无新事”,精神之路永远面临这样的悬难——尽头,或没有尽头,尽头必至无聊,没有尽头则难免疯掉。这也正是浮士德博士的困境:停下来,灵魂输给魔鬼,总就这么走下去呢,可到底是为了啥?然而,大地上或现实中,生活似乎只提供这两种可能;即便发疯,生命也还是去如逝水,空若荒云。
黑格尔给悲剧的定义是:相互冲突的两种精神,都值得我们同情。推演之:相互背反的两种选择均属无奈,那才是悲剧。而来个清官即可化悲为喜的故事,乃愚昧的成果,只能算惨剧。悲剧,是任人多么聪明能干,也只能对之说“是”的处境。比如浮士德:你停下来,还是走下去?比如现在:飞速前进的利润与消费、飞速恶化的生态与道德,是可能停下来呢,还是可能永无止境?与黑格尔给出的境况相比,此一种两难,可谓悲之更甚——前者或仅及个案,后者却要我们大伙的命!《浮士德》的伟大由之可见。《太》剧的不同凡响,由之可见。
怎么回事,要命的倒是伟大、非凡?真这么回事,至少对艺术和艺术家来说是这样。艺术家若都在现实中活得流畅,不觉任何荒诞,停步的人间就全剩躯壳了。科学、商政,各得其所,艺术凭啥吃饭?艺术,当是人类精神最敏锐的一处觉察,只为年节添些乐子,近于玩忽职守。惟当见识了精神的悬难,以及现实不断更换着新装的无聊与无奈,人才可望成为如尼采所说的“超人”。“超人”,并非是指才能盖世、法力无边,而是说,人要超越生理性存在,超越可口与可乐(譬如种种“大餐”),使精神不断升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也是这意思。可学习,不见问题怎么行?精神升华,不识其困境怎么行?
可是,单识困境,就行了?但这是不可躲闪的第一步。比如对姜文这部影片,大可不必人云难懂,就看也不看地自认智商也属低下。又有先哲说过:“不是艺术模仿生活,是生活模仿艺术。”艺术,自有其引领欣赏和启发思向的职责,若一味讨好票房,品位势必持续走低。而后,再看那悬难是在呼唤什么吧。张辉在其《德意志精神漫游》一书中这样提醒我们:“向歌德学习: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信仰不断‘向前走’的时代,如何同时关切永远‘向上走’的问题。”——即“人如何向上再次拥有信仰的问题”。这便是悲剧的意义。悲剧,不等于眼泪,更非教人沮丧。悲剧,把现实中不解的悬难彰显在我们面前,意在逼迫着我们向上看——看那天天都在脱离地平线、向上升起的太阳,是一个根本性象征。
《太》与《浮》的异曲同工,未必是姜文的刻意所为。然而,一个诚实又善思的人,早晚会跟大师歌德想到一块儿去。姜文依靠其敏锐的觉察,在局部的历史中获取着生命的全息。惟此才有象征。象征不是比喻。比喻,是靠相似事物的简单互证,比如指桑骂槐。再引一位先哲的话吧:“象征是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的标记。”另一世界,有吗?比如说就在你心里,在人们不息不止的盼念中。盼念,若旨在不断加强可口与可乐,就还是停留在此一世界。而姜文是以什么为比照,看穿了那无聊与无奈的呢?梦想,或向往。梦想或者向往,毫无疑问是指向着另一种生命状态。何东老兄有句极刻薄又极精辟的话:(在某些地方)总是没有梦想照进现实,常有的倒是妄想照进现实,或现实击穿梦想。
我妻子说,是“印象”二字,让她一下子看懂了《太》剧。诗,大都重视印象。诗性的根基是梦想。何谓梦想?恰如刘小枫的一个书题——《圣灵降临的叙事》。圣灵如何降临?简单说就是梦想照进现实。单靠记忆的回首,没有梦想插手,往事所以是死的。所谓永恒呢,即千变万化的当下,总与那梦想接通。这一接通,便不能满足于记忆的准确了,而是醉心于印象的天上地下,从而鲜活,从而全息,便有了象征的博大。姜文,固执地向那逝去的往事发问:这是怎么了,到底都是怎么了呀?幸好他不中理论的圈套,而靠自己的冥思苦想去解答。过士行说:《太》剧处处透露出神秘的力量。刘小枫是这样说:象征,是“无论你如何看,也看不够、看不全、看不尽其意味”的。
向上升起,是太阳给我们的永恒启示。再经时日,这个不屈不挠的姜文又将会怎样升起,尚未可知。或可更少些愤怒,更多些平静吧。我是指影片的开头,现代的疯狂就像那条照常流淌的河水,其实是波澜不惊的。无可挑剔的作品是没有的,但这不是本文所涉之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