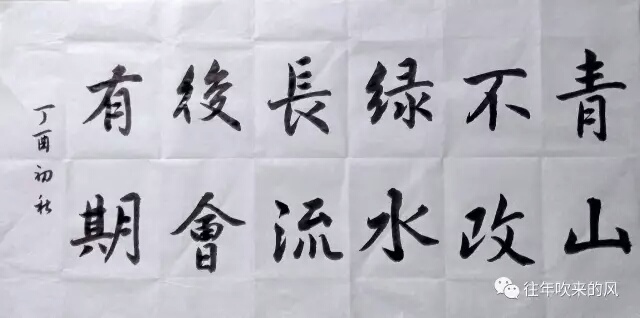西湖梦
2017-08-17 往年吹来的风
我对于西湖的念想源于一个虚拟的人。
他叫吴邪,是小说《盗墓笔记》的主角。住杭州西湖,在西泠印社边上开了家叫“吴山居”的古董店。
那段时间,我心心念念着这样一个名字,奈何却始终是没有这样一个人。无意间在图书馆找到一本小书-----张岱的《西湖梦寻》。想着就算是了解了解他的所在地也是好的,却没想到这本书让我真正向往起西湖来。
十月中旬,因着台风的关系,连下了几天的雨。
我们住的青年旅店在虎跑路。虎跑一路桂花开得盛,花香四溢。我本是不喜桂花香味的,但一路踏着满地的落桂寻青龙山脚的旅店倒也觉得舒爽。
头天晚上我们去了清河坊。清河坊之名取于南宋,沿用至今,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都是杭州最繁华的地带。这里多名门望族的深宅大院,还有回春堂、庆余堂这样江南地区享有盛名的国药店。这些老建筑如今大多都还立在那里,而我只是远远地望一眼便离开了。如今的清河坊,商业化太重,在这里我便不多写了。
第二日便是要去那心心念念的西湖了。
我们自青旅一路步行至苏堤,便一直顺着苏堤走。苏堤最著名的景色便数“苏堤春晓”了吧,只是我们此次无缘见了。苏堤很长,横跨了整个西湖。整条堤上树木繁盛,最多的当属杨树与柳树,也有刺槐,远望似一条绿色的长龙横卧在湖面上。
苏堤上还有处景观名“花港观鱼”。只是我们去的时候,没见着花,也没见着鱼,倒是几株枯树立在池边,枝桠凌乱,却也有几分韵味。透过乱糟糟的枝桠看雨滴落入池中开出一朵朵小水花,也算是弥补了无花无鱼的遗憾了。
那日苏堤的游客不多,只是我穿着宽大且丑的雨衣,走得也不太畅快。走走停停,不知不觉便到了望山桥。苏堤上有六吊桥,分别是:映波桥、锁澜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与跨虹桥。六吊桥建造不一,立于桥上所见之景也不一。望山桥头有一位老者在柳树下吹笛,笛声悠扬,一阵风来,柳枝随着笛声起舞。远处驶来一只乌篷船,船夫单手执了桨,另一只手拿着早点在吃。远处西里湖对岸的山在烟雨中影影绰绰,朦朦胧胧。我站在那吹笛老者边上听了许久笛音才离去。
苏堤的尽头是岳王庙,庙前塑着抗金名将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婉约妩媚的西子湖因着岳飞、于谦这些人也添了些阳刚之气与历史的厚重感。
自岳王庙往东走便到了西泠桥。张岱在《西湖梦寻》里引方子公诗:“数声渔笛知何处,疑在西泠第一桥。”又有前人曰:“看画舫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可见昔时西泠桥畔画舫笙歌的盛况。当年俞平伯先生客杭时也常乘船掠过孤山,在西泠桥买甘蔗。西泠的动人之处怕是我在这写不尽的。而今世知西泠,一者因“天下第一社”的西泠印社,二者便因着南朝钱塘名妓苏小小了。西泠桥头有慕才亭,亭下有苏小小墓。传说苏小小游湖上,与一书生相遇相知,写下“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诗中“西陵”便是今日的“西泠”了。如今立于桥头,只能感佳人不再,却又庆幸佳话长流。
过了西泠桥,是西泠印社。西泠印社是白堤的尽头,位于孤山脚下。背靠的孤山杜鹃也是一景。我自西泠印社的月洞门进。这雨又潺湲地下了起来,我便又将那肥大的雨衣套上。往里走便见着了那著名的石牌坊门。过了石坊,拾阶而上,到孤山顶可见“西泠四泉”。其实当时立于孤山顶时我是茫然不分方向的,只见着有座茅草亭,便坐在里边歇脚了。泉边有座小塔,隐在绿树的枝叶里。当时被塔下石壁上写着的“西泠印社”四字吸引着,没有多注意那座塔。后来才知,那便是华严经塔,而那泉便是“文泉”了。想来真是有些后悔,若早知,我必然在那泉前多站一会儿,日后想必也能“文思泉涌”了。
华严经塔东侧是是小龙泓洞,室友说想在亭中继续休息,我便独自一人穿过小龙泓洞往山后走。适时正逢雨落,洞顶有水顺着石壁下滴。一滴,两滴,三滴,隔断了室友的身影。社后杜鹃倒是多,只是深秋时节,只能赏叶了。我一个人顺着石阶而下,山下湖里有残荷。雨差不多停了,残荷上有水珠,顺着荷茎往下滑。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果然随处一瞥都是风景。山下秋风涉江而来,吹皱一湖秋水。我脱下恼人的雨衣,欢快地与室友会合去了。
又返回过了西泠桥,顺着北山路一路往东。秋风很劲,不时地吹落梧桐叶。那梧桐叶飘摇而下时,有的在空中飞舞几圈,落在湖面上,漾起一圈涟漪;有的落在残荷上,与那残荷私语一阵才又被一阵风抖落到湖里;还有的落在我的衣上,或是越过我的肩膀,落在我脚边。我们沿湖走着,马路对面有许多别墅,因为天色昏暗,许多都亮了灯,我起初以为是民居,后来买了份西湖地图才知那条路上有静逸别墅、孙传芳宅、坚匏别墅、蒋经国旧居。俞平伯先生说曾与朱自清先生在坚匏别墅的碧桃树下发过一回呆,后在忆西湖时写道“前尘前梦久而渐忘,此事在忆中尤力趋暗淡,追挽无从,更何下笔,二不堪也”。大概“北街梦寻”寻的便是这样的前尘前梦吧。
北山路的尽头有望湖楼,望湖楼对面是断桥。断桥是白堤的开始,最著名的便是“断桥残雪”了,而我们也是无缘的。在桥尾租了自行车,顺着白堤过锦带桥、明鉴楼一路往前骑,也不知道自己会通向哪里。秋天雨后清凉的风扑面而来,清脆的车铃声在这梦了千年的湖面上响着。响着响着,到了楼外楼了。“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宋人的一首讽刺诗造就了如今湖上两家百年老店:山外山和楼外楼。我知道楼外楼也是在《盗墓笔记》。吴邪宴请朋友时都在楼外楼。楼外楼门前车水马龙,我们只得推着车前行。行到西泠印社,才恍然大悟,自己又绕了回来。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便只得又过了西泠桥,循着北山路往断桥骑了。路过葛岭时,在我的坚持下,我们推着自行车上了小坡,在坡上见了一块旧路牌,画了个箭头,写着“保俶塔”。我大喜,原来保俶塔在此处。但是望了望那蜿蜒的小径,尽头隐在了云雾缭绕的竹林里,我们最终还是没有上去。
西湖双塔,保俶塔似美人,雷峰塔如老僧。我没去成,心里虽是遗憾,但想着或许近看的保俶没有远观那样亭亭玉立。如此一来,那遗憾也就散了些。
我们还了车,有两个室友回了酒店休息。我留恋这西湖,便和另一名室友继续绕着湖游荡。
天色渐暗,湖中画舫也次第上了灯。
我们借着昏黄的路灯看着地图,终是在天完全黑之前走到了雷峰塔下。那时雷峰塔已经上了灯,灯火颇为璀璨,倒映在深幽的湖水里,秋风一吹,便漾开了一湖繁华的千年凡梦。
天已经全黑了,我们却还坚持拿着地图,摸索到了净慈寺。净慈寺就在南屏山下,只是我们去的时候,寺门紧闭,也没有灯火。我们拿着手机照了半天才看清那写着“净慈寺”的匾额。如此,也是听不到南屏晚钟了。有些怏怏地回头,却忽见一轮秋月嵌在墨色的夜空中,与雷峰塔的璀璨灯火遥遥相望。这西湖月,自古至今也不知慰藉了多少文人的灵魂。
在月桂簇拥的青旅住了一晚,接下来便是灵隐了。
早早搭了公交,电子地图显示在“立马回头”公交站转车。公交站很安静,两旁树木茂盛,路牌边上就是一小片茶园,茶树上零星地开着几朵白色小花。明明离市中心不远,却不见半点城市的喧嚣。等了一会,便见一辆写着“灵隐”二字的车缓缓从树荫里拐进我们的视线。
灵隐寺在飞来峰脚,树木猗郁。我们一行四人,偏没跟着大部队,挑了条小径往里走。越走越深,见着几尊菩萨石雕。终于寻到了地图上的“玉液幽兰”,她的门却紧闭着,我们只得观了那门前落了一地的桂花。越深处小径越窄,径边有种绿得出水的植物,只是我不知晓她的芳名。风摇落大树叶子上的雨水,落了我们一身,那清凉的雨水滴进衣领里,沁人的凉意让我缩了缩脖子,却依旧坚持往里走,直到看到尽头一片茂盛,便只得回头去追那大部队了。
灵隐寺前有泉奔流过,名“冷泉”。冷泉上有亭名“冷泉亭”。白居易曾作《冷泉亭记》:“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余杭郡言,灵隐寺为尤;由寺观,冷泉亭为甲。”本想着去那亭上坐坐,听听那一泓泠然,奈何亭上人太多,只得一路往前了。
上到永福寺,几人已累得气喘。现在想来,永福寺中,使我映像深刻的竟只剩下山泉和山茶了。永福寺其实不多山茶,我只在普园净院见着。只是那山茶开得极美,白里透粉的花瓣上还挂着露珠,晶莹剔透,十分可爱。那山泉在寺内的茶园里,置有竹筒让游客舀来解渴,泉清冽可照人。
永福寺后是韬光寺,旧时称韬光庵。袁宏道《韬光庵小记》写:“韬光在山之腰,出灵隐后二三里,路径甚可爱。古木婆娑,草香泉渍,淙淙之声,四分五络,达于山厨。”雾树相引中的石阶小径确是可爱,而我们却应了张京元的小记:“鸟道蛇盘,一步一喘。”匆匆逛了韬光寺便下了山,终是没上那北高峰。
我们将灵隐寺周围都逛了,却没进去灵隐寺,便去寻了三生石。
三生石在天竺寺下,东坡的《僧圆泽传》记载李源与僧圆泽交好,圆泽告知李源自己将要投胎王家,叫李在婴儿三日沐浴的时候到王家看望,他会以一笑为信,十三年后天竺寺见。李源遵信,果见婴儿见到自己时灿烂一笑。十三年后,李源自洛阳赶往杭州应约。在天竺寺下见一牧童在牛背上唱:“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李源大呼:“泽公健否?”牧童答曰:“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语姻缘恐断肠。吴越山川寻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唐。”遂不知所踪。如今的三生石在人们心中的定位或多或少与这有些偏差。无论后世多少关于三生石的轮回故事,我却认为这个最是动人。
西湖边上处处是故事,或繁华,或凄凉。西湖作为一个文化意象,一直出现古今文人的笔底,摩挲中国文化一久,就自然而然带出这一片湖。余秋雨写西湖时,用的也是“西湖梦”一题。他说:“对许多游客来说,西湖就算是初游,也有旧梦重温的味道。”
我的西湖梦源于吴邪,陷于张岱。如此说来有些幼稚,而吴邪这个人到现在为止确是占去了大片我对西湖的梦想。
张岱在《西湖梦寻》自序中写:“余生辰不祥,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日别余也。”但当他正真重新面对西湖时,又有“则是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的感慨。如今的西湖虽好,但我还是想回到旧时的西湖看看,而这个旧时到底多旧我就也不知了。我该多么感谢张岱“作《梦寻》七十二则,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让我面对如今的西湖时也有个旧梦可温了。